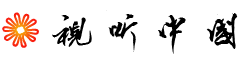新学院派回归能否将电影带出“垃圾堆”?
电子版首页 >
第B02版:启示录
下一篇
新学院派回归能否将电影带出“垃圾堆”?
2017年06月27日 星期二
北京青年报



◎唐山
重拍《傲蕾·一兰》(原片1979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重拍《悉达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的第9部著作),重拍《金锁记》(原著为张爱玲的代表作)。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三大重量级电影筹备项目正式发布,这被视为“新学院派”一次集体发力。加上不久前在威尼斯电影节、东京电影节上获奖的《不成问题的问题》(改编自老舍先生的同名短篇小说),“名著改编热”似已成气象。
正因后人一再改编,好作品传之久远。
不否认,改编必然带来扭曲,后人总要在经典中加入自己的误会,但经典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结构是开放的,足以容纳不同时代、不同人的创造,却又不失去其本然的魅力。
不断改编名著,其本质是创造一个文化传统,这是最好的普及课,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严肃创作与消遣之作的不同。通过一代代人层积的阐释,这些文化传统最终会融入到个体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中。
如果没有宋词、元曲乃至流行歌曲一次次改编李杜文章,如果不是民间故事、评书、戏剧、连环画、电视剧反复刷新四大名著,我们如何将这些经典刻进记忆?我们还会为我们的传统感到自豪吗?
然而,在今天,改编面临困境,正如冯小刚说:“中国怎么这么多垃圾电影?还不是因为有那么多垃圾观众。你不去捧场,就没这东西,往往垃圾票房还很好。”
冯小刚的话有倒因为果之误,但他说出了当下电影的困境——商业价值压倒艺术价值,创作水准不断下滑,大环境日趋“垃圾堆”化。
这个困境并非电影独有,在音乐、文学等仰赖创造力的领域中,均出现了同样问题,体现出消费主义对文化积淀的蚕食。
我们已进入一个被消费拿捏的氛围中,消费主义试图将人们编织进消费秩序中,即把每个人都格式化为“生产者+消费者”,通过不断创造出更光鲜、更闪亮的新商品,刺激人们更多消费,由此将其套牢在格子间中,埋头于枯燥的生活。
比如人吃饭,本是为了获取营养,但消费主义创造出快餐,随时随地能让人满足口腹之欲。味道完全符合预期,更大的分量、更划算的价格还能附赠惊喜。在此诱惑下,人摄入更多热量,随之诞生出减肥、健身房、吃药、绿色食品等新需求。在今天,还出现了抗性淀粉这种奇葩食物,它无法被人体消化,让人大快朵颐后,不用担心摄入过多热量。可这和吃饭的初衷岂不完全相悖?谁还能说清,我们原本需要的是什么?
越挣扎,就越沉浸其中,这是消费主义的可怕之处。当活着的目的变成帮消费主义扩张,我们犹如《黑客帝国》中的“电池”时,则消费主义必然会创造出一种麻醉剂,让我们相信当下的一切如此美好,这样我们才永远不会醒来,即使身边是“垃圾堆”,也觉得这才是正常的。
“每天这么累,我想看点轻松的东西。”“严肃作品太沉重了,看不懂。”“它们与生活有什么关系?”种种声音,正是“垃圾堆”化的真实写照。对于生活其中的人,告诉他们烤鸭好吃是毫无意义的,即使他们尝上一口,也会觉得不对胃口。
怎样摆脱消费主义?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目前并无根本的解决方案,只能靠“文化醒觉”来对冲,这需要专业群体的介入。毕竟严肃创作与现实存有距离,所以它能不被生活融化,能批判生活。可这个距离也会让受众找不到自我,感到丧失了尊严。面对严肃创作,他们往往用“看不懂”来回绝。
在上世纪80年代,严肃创作与大众联系更紧密,因当时还有“学院派”。在电影界,比较突出的代表是《香魂女》《邻居》《黑骏马》等,这些作品为严肃创作树立了标杆,即:强调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形式上需遵循一定规范。
中国的“学院派”是舶来的,对本土文化只有功利性的征用,且征用标准来自西方。在提倡高雅的同时,并未脱去服务王权、维护等级制的烙印,对现实生活的多元与活泼持鄙夷态度。故一旦离开权力扶持,很容易被市场经济淘汰。
然而,挣脱“学院派”,人们才发现,消费主义是更可怕的暴君,从上世纪90年代一路走来,电影市场不断扩大,好作品却越来越少。2012年以来,《失恋33天》《万箭穿心》《飞越老人院》《我的影子在奔跑》《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作品相继出现,标志着“新学院派”崛起。
与传统“学院派”比,“新学院派”更重视交互性与体验,强调“虚拟现实”,从而突破了传统只重现实的封闭。与“学院派”一样,“新学院派”也提供了一套标准,它试图告诉人们,什么才是严肃创作,如何看懂严肃创作,以及严肃创作向何处去。
“新学院派”细节考究,充分吸纳流行元素,却用它来为严肃内容服务,但由此也可能带来两个瓶颈:
首先,对于缺乏“理解之同情”者来说,“新学院派”是在“谬改”“不尊重”“歪曲”名著,俨然谁也不再改编名著,任其慢慢被遗忘,才是最大“尊重”与“负责”。这或者就是为什么,“新学院派”选择的多是那些不太受关注的名著,如《不成问题的问题》,并非老舍先生名气最大的小说,读过的人并不多,这就免去许多笔墨官司。
其次,“新学院派”更善妥协,因有条件地接受当下,宽容了现实的某些结构性缺陷,故其批评不易深入,多停留在质疑科学主义、消费主义的层面,对造成这些偏执背后的力量只好视而不见。这往往迎合了学生们的心态,他们深受其苦,却又有出路可投机,有一个巨大的牢骚,已经足够。
艺术总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而创造经典,其实是个低概率事件,无需对“新学院派”提出那么苛刻的要求。毕竟他们还在抵抗中,还在建设着,未沉醉于靠骂观众来标识自己卓越,那么,对他们来说,未来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