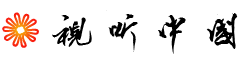时间的刻刀:奥克尼民谣节,穿越历史的音乐狂
对于乔治·麦凯·布朗的短篇故事《海豹皮》中那个半人半海豹精(Selkie)的音乐家马格纳斯·奥拉夫森来说,艺术,不是一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需要依靠艺术家的敏感情绪来实现,而是存在于时间之初,无人知道来源。艺术家所需要做的,只是以人性的名义不断修补一张创作之网,在里面,交织着那正在一点点被人毁灭的,宇宙中人与神、星与月、草木与野兽间的和谐之音。

远古的巨石和牧人的羊群
海豹精的传说广泛流传于奥克尼群岛。据说他们以海豹的样子生活在大海中,时常上到海岸,脱下海豹皮,变身人形,载歌载舞。若将他们的海豹皮拿走,他们就再也回不到大海。历年来,常有海豹精或有意或无意地丢失了海豹皮,被带到人类中间,与他们相爱、生子,而也终会在找到自己的海豹皮后,抗拒不了大海的诱惑,回到水中,消失于人间。人形的他们通常十分美丽,且有着秉异的音乐天赋。马格纳斯生于奥克尼,他的母亲就是这样,在他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回到了大海,从此销声匿迹。他的父亲不愿提起她,他也就从不知道自己的音乐来自何方,只是用心编织着那个网。而奥克尼群岛的人,也来自于海上,却早已不知具体是何方。来自苏格兰主岛的皮克特人,来自北欧的维京人,以及也许藏在他们之中的半人半海豹精们,他们的后代在这些小岛上安居,讲着故事唱着歌,还在每年夏季来临的时候,举办盛大的民谣节。他们不在乎你是哪里人,只要你有故事,有音乐,奥克尼就会成为这样一张网,热情欢迎你来系上自己的那一根线。

爱丁堡大学民谣协会在酒吧表演
与我同行参加奥克尼民谣节的有民歌手斯科特·加迪纳(Scott Gardiner),他在爱丁堡附近的农场长大,说着一口地道的苏格兰方言,会唱许多苏格兰东部的民谣。他在民谣节上身份特殊,因为他每晚都会主持一个歌会,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围坐在沙发上,或是献唱一曲,或是安静聆听。斯科特告诉我,自从十五年前第一次随爱丁堡大学民谣协会来奥克尼参加民谣节,他从未间断过,但直到两年前,他才开办了这个歌会。除了一些正式的演出,对于来参加艺术节的民谣乐手来说,最快乐的时光是从早上一睁眼(或者索性一晚没睡),就开始穿梭于斯特罗姆内斯镇(Stromness)的各个酒吧,奏乐喝酒。这样的演出方式非常热闹,也不局限于只和自己乐队的人共演,若你遇上自己喜欢的曲调,可以随时拿出乐器,加入其中,曲子信手拈来。年纪大的乐手早已一头白发,而年纪小的,则满脸稚嫩,他们之间可能从未说过话,却用音乐交流内心。观众来来往往,狭小的酒吧里往往都找不到站立的地方,但还是会许多人,端着大杯的麦芽酒,时而驻足观望,时而就着乐声与同伴高谈阔论。然而歌手们常常会因为酒吧的嘈杂而得不到安静唱歌的机会,所以斯科特想到,也许歌会能够让歌手们得到更多交流的机会。

参与打节拍的小女孩和指导她的老奶奶
参加民谣节的歌手大多来自苏格兰,爱尔兰,或是北欧,偶尔有几个来自别的国家。来歌会的人有的是早已畅销专辑的歌手,有的却从未登台唱过歌。斯科特说,因为歌会友善的气氛,许多初来乍到的人被激发了潜能。在他的盛情邀请下,我也去参加了一次歌会。我坐在角落里,被每一个人唱的歌都深深吸引,离开了乐器的伴奏,人的歌喉也就成了最纯的乐器。绕了一圈到了我的角落,斯科特忽然叫我名字,说,也来一首吧?作为歌会上唯一的亚洲面孔,许多人充满期待地看着我,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在一群陌生人面前声音颤抖地清唱起了《马桑树树儿搭灯台》。歌会结束后,一位胡子苍白,拄着拐杖的老人走到我面前,我记得他刚才用沧桑的声音唱了一首关于战争的歌。他特别认真地对我说,我仿佛在你的歌声背后听到了乐器的伴奏,这是一首情歌吧?我惊讶地点头,并且提出可以给他翻译歌词,然而他又说,用不着,这些东西,就需要用你们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曲调唱出来,然后每个人就都会懂。

Yesnaby悬崖
在这个年代,曾经作为苏格兰高地人的母语盖尔语已几近消亡,然而盖尔语的民歌却因为与老人的话相同的理由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民谣节不乏盖尔语歌曲的演唱,尽管很少有人真的能够听懂,却非常受欢迎。在盖尔语民谣界负有盛名的朱莉·弗丽丝(Julie Fowlis)也来参加了今年的民谣节,她是皮克斯电影《勇敢传说》中歌曲的演唱者,一举让盖尔语民谣走向世界,而如今她站在台上,温柔地诉说自己对留在家中的幼子的牵挂,唱着她给孩子们唱的摇篮曲,讲着那些人们熟知的传说。

人们就着民谣翩翩起舞
在弗丽丝唱的歌中,有一首从18世纪流传至今的歌,来自约翰·麦科德伦(John MacCodrum),麦克唐纳宗族最后一位吟游诗人,吟唱美丽的土地和英勇的麦克唐纳宗族。1746年第二次詹姆士起义失败后,高地的宗族制消亡,再也没有了吟游诗人,但歌却被流传。还有一首歌,唱一个被水马怪(waterhorse)拐走的小姑娘祈求它放她回家见妈妈,姑娘最终也没有能够逃走,但故事仍在被讲述。苏格兰民歌大多叙事,主题无非几种:失去的爱人、神秘的传说、战争的暴行、英格兰的欺压和英雄的悲怆,但当缓缓的曲调和悠扬的声音将这些故事缓缓道来的时候,你会听到时间本身的声音。弗丽丝说,有一句盖尔语谚语叫“Gheibhear deireadh gach sgeòil an asgaidh”,她理解为,“每一个故事都将实现”。因为故事独立存在于世,无论我们参与与否,它们都将行走于世间,与时间一起走下去。而歌声,就如布朗所说的那刀刃,在时间的石碑上刻下一道又一道印迹,后人便从那些印迹中,探寻过去。

午间奏乐
奥克尼群岛是一个随处都有时间印迹的地方,这里遍布新石器时代起留下的石屋、石冢和石阵。近五千年的遗迹,在这里仿佛后院的一个随意的雕像,任凭风雨打磨。维京王哈拉德·赫法格尔(Harald H?rfagre)在9世纪将奥克尼群岛吞并进挪威,他的后代遍布奥克尼和后来的冰岛,直到15世纪,挪威国王将它作为公主的嫁妆送给了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三世。没有人知道新石器时代在这里住着的人是谁,去了哪里,但他们曾经可能有惊人的文明。传说布罗德盖石圈(Ring of Brodgar)是一群在夜晚跳圆圈舞的巨人,因为忘记了时间,被第一道阳光化作石头,而给他们伴奏的提琴手则成了一旁的科美特石(Comet Stone)。梅肖韦古墓(Maeshowe)狭长低矮的通道,冬至的最后一道阳光会径直穿过它,照在墓穴正中央的大墓冢上。古墓终被尘土埋没,直到一群维京海盗找到这里,打开墓穴进来避风雨,并且有人爬到高处的墙上用如尼文刻下“我把这些文字刻在高处”。我们用音乐在时间的石碑上所刻划的,也许与这维京人一样无用可笑,然而,却终有一天可能唤醒爱跳舞的巨人,听他们告诉我们曾经的一切。

斯特罗姆内斯一户海边人家
因为我们又与变成石头的巨人有什么不同呢?沉浸在音乐的美好中忘却了自我:发烧的弓和弦,不知疼痛的手指,如雨的踢踏舞步,如雷的鼓点,凌晨三点在街上奏乐的风笛手……还有或许第一日晚上才就着美酒通宵达旦跟别人学会的曲调,第二天就拿去在众人面前表演。这就是民谣的魅力,也是它的生命力,它不属于任何人,它只属于时间,但每个人都可以短暂拥有。民谣节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背着干柴带着酒,来到海边营地。那晚的火星特别明亮,如一枚红宝石般高高悬挂在海峡对面霍伊岛的两座高峰之间。这几乎要进入北极圈的岛屿,在即将六月的深夜,天依旧蒙着一层紫色的微光,寒气冷得刺骨。我们点燃篝火,紧挨着彼此,围成圈,伴着海浪拍打石崖的节奏,弹琴唱歌。唱远行的水手在风浪尖打拼;唱因为爱上永远不会看自己一眼的高贵公子而自杀的女孩;唱丈夫与妻子之间诙谐的对话;唱来自海上留着长长灰胡子的神秘老头;唱家乡一棵充满儿时记忆的花楸树;唱即将被执行绞刑的姑娘求年迈父亲给刽子手一点钱好来个干净利落;唱那战败后逃亡天空岛的查理王子;还唱一个变身人形的海豹精上岸索要他的孩子……

我们一群人在海边小屋里围着篝火,唱歌到天亮
第一抹太阳升起的时候,海中礁石上几头海豹慵懒地拍打着尾巴。他们是不是在等待时机,脱下海豹皮,混入人间?不知道我们的歌声,会不会在很多年后,依旧环绕在奥克尼多砂岩礁石的海边,由它们继续传颂。又或许,这些歌本就来自于海上,一如凯尔特人相信,音乐本就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永生精灵,人类只是学会了模仿。所以这些歌,终会再回到海洋,时间和生命最初的地方:
“站在陆上我为人,
置身大洋为海豹,
而当远离海滩时,
我安家苏尔礁岛。”(奥克尼民歌:《苏尔礁岛的海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