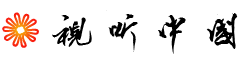指挥大师笔下的 荒诞历史
2017-08-20 17:01 点击:
(原标题:指挥大师笔下的 荒诞历史)
菲戈
偶然从书堆里掏出本多年前买的《索尔蒂回忆录》,随手翻翻,就再也放不下来了。这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红色与白色的血腥战斗,几乎搞不清楚自己属于哪个国家的犹太人,最终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
这本自传再次证明了,最好的文字经常并不出于文人之手,而是出自生活经历最丰富、经受苦难最多的那些人真正直抒胸臆之时。回忆录中那完全不经意的一段一段回忆,抽出来往往就是一篇绝妙的短篇小说,虽然它们完全是真实的,相信索尔蒂在落笔的时候也一点都没把它们当成某种文学性的东西。然而这里有雷蒙·卡佛式不动声色的细节,有欧·亨利式最后关头抖出的包袱,有时候又有卡夫卡式铺天盖地的荒诞感。对经历了那样一种人生的人,又何必去动用虚构的想象力呢?
比如关于“海军上将霍尔蒂”的一段。
1918年秋天,奥匈帝国正在衰亡之中,我们回到了布达佩斯。我们坐着马车,在夜间赶路,不敢白天走。因为白天全国红色和白色两派政治势力在交战。在那恐怖的年代,反动分子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杀反动分子。我所记得的仅仅是回到布达佩斯的行程和对随时会发生意外的恐惧。从那时起,我就无法消除对穿军装、警察制服甚至海关制服的人的恐惧感,因为在匈牙利,制服总是意味着某种形式的迫害。
在一段时间内,红色势力占了上风,匈牙利由共产党人贝拉·库恩组阁。像许多左翼积极分子一样,他是犹太人。多年之后来看,这事被证明为是犹太人的一个巨大灾难,但在另一方面这又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犹太人反对极右派。极右派总是排犹的。贝拉·巴托克和佐尔坦·柯达依都不是犹太人,他们在库恩的政府中任职,单纯地相信平等。最后,海军上将霍尔蒂骑着一匹白马入主布达佩斯,统治了全国。他是极右派领袖,也是匈牙利历史上惟一的一名海军上将,因为匈牙利是内陆国家,没有海疆可供扬帆。
此外,索尔蒂这本回忆录堪称上世纪古典音乐界奇人怪事“宝典”,以他周游世界的脚步,以及因为他的成就而与各位大师名人的交集,记下了多如牛毛的趣闻轶事。音乐大师们的个性本就古怪奇特,由索尔蒂兼具直率与冷幽默的文笔写来,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再摘一段关于著名作曲家佐尔坦·柯达依的。
我母亲坚信我是第二个莫扎特,她说服(布达佩斯的)一位政治家为我写了封介绍信,举荐给音乐学院最著名的作曲教师佐尔坦·柯达依。
柯达依那时四十五岁左右,是位才华横溢而有些狂放的人,他后来度过了几年的艰难岁月。他那时还算年轻,苦行僧般的脸上留着列宁式的胡须,看上去像基督,有几分执迷的意味。他视共产主义为救世主,在生活上是个极端自律者,严守素食和冷水浴,打赤足。那阵子他上音乐学院不穿鞋……真不知道我母亲哪来的这么大勇气,把我带到一位这么声名显赫的人面前,来到他位于音乐学院的研究室。我母亲在政治上很无知,她丝毫没有意识到,写举荐信的人是右翼政治家,而柯达依是左翼人士。我母亲对他说:“我儿子在作曲,他带了几首自己创作的曲子,你愿意听一下吗?”
我现在肯定那几首曲子是很糟糕的,但柯达依很耐心地听了。他对我母亲说:“孩子确实有才气,但得等到他毕业。到他十八岁时再带他来吧,那时我们再谈他作曲的事。”这是公正的评价,但我母亲却被深深地刺痛了:柯达依怎么竟然贬低她的小莫扎特?她没听他的,马上又带我去找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阿尔伯特·西克洛斯教授。他听了我的作品,就收我入学了。
……几年以后的一个晚上,我坐在国家歌剧院餐厅里我常坐的位子上,当晚剧院要演出柯达依的《特兰西瓦尼亚的纺屋》。我那时是剧院的排练指导,导演伴着柯达依向我走来,让我带作曲家去他的包厢。路上,柯达依对我说:“你看,你用不着那封举荐信,没有它你也干出来了。”
“你还记得呢,教授?”
“啊,是的。”他轻轻地说。
此后的三十年,我没见到过他。1964年,在萨尔茨堡,我指挥马勒《第一交响曲》。演出结束后,招待员到我的更衣室对我说柯达依教授要来见我。柯达依同他那位新的、年轻的妻子(他的第一位妻子死了)进来了,说了句令我吃惊的话:“我得请你原谅,我那次对你母亲如此失敬。但是,你看,那个写举荐信的人是我的政敌。”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
上一篇:追寻红色足迹 感受人文历史
下一篇:导演土井敏邦力挺《二十二》:“日本应正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