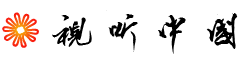所谓的小人物也是伟大人物

很高兴能来到北京,因为中国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在苏联时期,我有一本书就是在中国出版的。我觉得这可以说是一个轮回,我又一次转了一个圈回到这里。中国30年来的变化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我们也经历了30年的改革,但是你们的30年改革出了新的房子、新的道路,我们的30年改革,还是旧的房屋、旧的飞机、旧的汽车。现在在欧洲流传着一种说法:别谈未来,未来已经消失了,谈到的一切都不会实施,一切已经逝去了。
在中国,我看到了有未来,有希望,我对你们表示羡慕。
至于说到我的创作,已经40年了,我一直在写所谓苏联社会主义的演化过程。我认为,我们不能前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什么是我们的理想。
多么奇怪,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对一切还不明白,我们甚至害怕知道这一切。我们甚至害怕知道“二战”的真相。当我还是一个年轻记者的时候,我就开始了思考,我应该用什么方法把它记录下来。我记录了普通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小人物”。我同那些人们认为根本都不值得和他们进行交谈的人进行交流,和那些根本都不需要听他们意见的人进行交流。这些人从来也不知道,也不去想那种伟大的思想,他们只是知道使用思想。
当我和这些人交流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这些人并不是小人物,他们也是伟大的人物。
思想来自实践,而非空想
我写了5本系列的图书,其中的两本谈到了战争,其中还有一本谈到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件,另外一本谈到了苏联的消失,当然这里还有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我选取的都是在我们历史中最关键时期的一些材料。在红色帝国消失之前,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同一体系的思维,而消失以后,每个人都开始有自己的意见了。
我决定保留所有人说的真理。我在书中写了各种主义的人,每个人的观点我都去记录。其实我不是去想这个历史,而是去记录每一个人,我不敢说,对于每个被采访的人说的一切,我都会喜欢,有时候我理解不了他们,有时候我也不能接受他们所说的,但是我把自己的手背起来,我把手背到后背,因为我需要他们的声音。
我与中国的读者交谈不是很多,但是在我的交谈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中国读者认为,我们两个国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在我们那里,信仰已经消失了,人们不知道该信什么,有的只是失望。
有一个阶段,叶利钦曾召唤知识分子说,你们应该想想民族的思想,现在普京也在召唤所有的知识分子说,你们应该思考民族思想了。但我认为思想不应该是坐在桌边想出来的,它产生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它来源于那些过得不是很舒服、对许多事情不明白的人们之中。
因为爱,让我坚持了下来
我采访的这些人有一个特点,苏联的经历在他们身上留下很深的记忆,这是他们的共同点。我也亲身经历了苏联解体,与被我采访的人一起,我们共同见证了、经历了共同的历史进程。
通过受访者的口述,我感到,他们对国家的很多东西是不了解的,甚至很多东西是断裂的。
在这个进程中,很多人曾在生活中经历了困难阶段,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生存。很多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抱有很大信念的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坚信的东西什么时候会迎来第二次春天。
其实我也被很多人问起过:你从哪里来的动力,推动你把这样一个很宏观的事表达出来?
我觉得,因为我也是这个过程中的经历者,我尽我的能力描述出来发生了什么,我的父辈们在这个进程中感受到什么。
我很爱我的爸爸,我父亲这一代人,特别是我父亲本人,他们是这一时代的、悲情式的人物。除了对我父母这一辈人的爱之外,我也客观地去描述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无论好的坏的。我的父辈,还有我们自己这一代人,我们尝试过一些努力,试图转型,但是很遗憾没有成功。
苏联曾经是那么强大的一个国家,但是现在从一个强国变成一个不太重要的国家,我应该写出这个过程中所犯下的错误,让更多人看到,这样未来的人们就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坦白地说,这40年来的创作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一条路,有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撑不住了。唯一能支撑我的力量是爱,我爱生活,我爱跟我共同经历这个进程的人们,我觉得是爱播撒了这样一个迎来春天的种子。
我是一个有大耳朵的人
我很少和当权者打交道,但是我在俄罗斯、在乌克兰,看到了战争这个问题。在我们那里,正在把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口号又给换成了一些宗教的口号,但这仍然解决不了战争的问题。在我们那儿,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慌失措,他们不知道应该努力奔向何方,他们有的人说普京非常有力量,有的人说普京非常软弱,有的人赞同乌克兰,有的人则相反。
至于说到现在知识分子在俄罗斯,他们主要读两部分书:一部分是德国有关上世纪30年代主题的书,也就是法西斯是如何产生出来的,还有的读上世纪20年代俄罗斯相关的书,也就是苏联十月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在俄罗斯,最可怕的是现在有些人正在变得物质化,这不仅是在知识分子之中,也在一些青年人中。
福楼拜说“我是一个笔人”,那么我说“我自己就是有一个大耳朵的人”。至于说到我写《二手时间》这个持续了十余年,这里经过了战争,经过了建设,经过了改革,我一直在倾听,当然我倾听的不是一个人的声音。
我也尝试过走进我自己的书里面,但是我的尝试始终没有成功。要是我参与进去,还能够看清俄罗斯的巨大痛苦,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灾难的“好处”是警示未来
我来自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明斯克是一个小城,白俄罗斯是一个小国,我们那里信息并不是很多。
我是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一群人当中的一分子,我们试图去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我们要怎么做。我很爱我的生活,我是很幸福的一个人,因为当你干了自己喜欢的事,搜集材料,约这些人去访谈,我把它们整理出来,以自己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这都是我喜欢的事,我干着我喜欢的事,所以我是幸福的人。
我是一个世界人,不是说我是哪一国的,给自己一个限定,而就是时代的一分子。其实我写过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书,也是我曾经创作的一个主题,我也亲历过切尔诺贝利区域,你在那的时候,你随时会被一种感觉所包围,你已经忘记了你是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的,你只是觉得,因为这样的灾难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一个人。
灾难,特别是像切尔诺贝利这样的核灾难,它的发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帮助我们唤醒我们反思自己,开始从自身上考虑问题。关于切尔诺贝利那本书在十个国家出版,它告诉大家的是一种警示和警醒,太阳照常升起,当一切很正常的时候,人的生命可能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喊自由的人常常不想自由是什么
之所以给我的书起名《二手时间》,因为一说二手,大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二手衣服。我叫“二手时间”,是我对自己国家当时发生事情的一个诊断。
我们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彼此各自成为新的国家之后,本来应该有一套自己民族的东西,应该有新的想法、新的看法和新的观点,可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什么都没有新的,我们都回去了,以前是什么样,现在又变成这样,这就是《二手时间》这个名字的初衷。
我非常遗憾,应该有新的东西,但还是回去了。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家喊要自由,但是这些喊自由的人有几个懂得什么叫自由?大家都以为明天会有自由,但是你想在监狱里铁窗下的人,他一辈子都不会走出铁窗,自由对他就没什么意义了,所以他也是自由的。
我们带着浪漫主义色彩去理解这个自由,自由貌似离我们很近,但其实这条路离我们却很远。只有到现在我们才明白,获得自由的道路如此漫长。
面对我采访的这些人,我也问他们什么是自由,很多人给不出答案,因为他甚至没有深刻地想过这个东西,他已经很习惯地去接受。所以还是刚才说的这一点,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一条很艰难、很长的路。
写作是为了展现爱
我的书里有很多角色,有很多声音,每个人都在谈论自己的一些事情,他们是多声部的作品。我们受那种从众文化的影响,一件事发生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也说什么,其实应该像我的作品那样,应该多声部,每个人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很多人在从众文化,丧失自己应该有的责任感,比如说斯大林好不好,其实斯大林也有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每个人应该从自己的角度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看重我所有书里的声音,它们表达着真实的想法,每个人都有捍卫自己真实想法的权利,这样我们才能客观地看到真正发生了什么。
我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我的思维没有限制在具体的事里,我更多是把经历这些事情的人的人性呈现出来。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爱着谁,我们为谁而感到遗憾,我们在等谁,所有这些人性上的一些东西,都会在历史和社会事件的大背景下体现出来。
我跟很多人聊、很多人谈,谈的时间很长,谈的东西也很多,写了很多,形成了很多材料,但是我真正写出来的并不是全部,而是个别的几行字。存在着一种对比,拿过来材料的本真的面目以及通过艺术的手法创作出来的艺术性,中间还需要再加工。
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善有恶、有好有坏,不可以剥离开。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一阶段遇到的都是不好的恶的这一面,负面的东西很集中,但是有赖于人性的美好,你会去战胜你觉得不好的阶段。
人从本性上来说,是很容易失落和失望的,但是我还是很爱这样的人。我在阿富汗看到了杀人和被杀的场面,确实很难忘,但我就是希望我的书,给大家看到的不是恨而是爱。我创作的目的并不是把那些阴暗的、吓人的、阴森的东西聚集在一起,把读者吓一跳,我希望大家感受到真善美的方面,帮助大家成为真正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