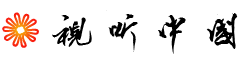课程:跨文化比较的视点
杨天平,范诗武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运用跨文化的视野来审视和比较课程概念,东方学者将课程诠解为学科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教学知识等,并着眼于分科课程、学科课程、显性课程和必修课程的建设,尤强调课程的社会功用;西方学者则将课程定义为知识、经验、活动及三者的统一,并侧重于活动课程、综合课程、隐性课程和选修课程等的架构,且一贯注重课程对个体成长和发展的促进功能。
关键词:课程;跨文化比较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杨天平(1956—),江苏盐城人,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教育管理基本理论、教育科学方法论和教育方针政策研究。
课程是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概念,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东西方由于不同的教育文化背景,在对课程本质、课程结构、课程功能、课程形态等的认识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当然,也有许多共通之处。因此,本文拟运用跨文化的视野对中外学者的课程观作一比较。
课程的定义繁多,人们在定义课程的时候,往往有各自的见解和思路。这种见解和思路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研究者个人之间,而且折射出各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中西学者关于课程概念不同的诠解,恰恰是东西方文化特征的一种反映。
首先,从对课程内在的质的规定来看,中国学者更多地主张课程是用以教学的科目,是具有系统性的学科知识或教学内容,他们认为,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是让受教育者获得知识,并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实现发展。这种观点在前面所引述的我国当代的《辞海》、《教育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以及许多教育专著和教育学教材中都可以看到。《辞海》认为:课程是教学的科目,可以指一个教学科目,也可以指一个专业的全部教学科目或一组教学科目。《教育大辞典》将课程定义为:为实现学校教育目标而选择的教育内容的总和;学科的同义语,如语文课程、数学课程等。《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认为课程定义有广、狭二义,广义指所有学科(教学科目)的总和,狭义指一门学科。无论广义还是狭义,都强调课程所具有的教育内容的质的规定,即将课程定义为由学校有计划、有组织地编制的教育内容。
西方学者则突破此种规定而赋予课程多种含义,比如,他们认为,课程既是教育知识,又是人的经验和活动等等。尽管有学者认为课程是用于教学的知识,比如美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课程论专家费尼克斯曾指出:“一切的课程内容应当从学术(学问)中引申出来。换言之,唯有学术(学问)中所包含的知识才是课程的适当内容”,[1](115)但还是有两种颇有影响力的观点。一种是课程即经验,认为只有个体亲身的经历才称得上是学习,外在的知识才能转化为学习者自身所有的经验。课程就是让受教育者体验各种各样的经历,在这样的过程中,将学习对象──包括知识但不仅限于知识,转化为自身的经验,并且实现自身的变化发展。卢梭在他的名著《爱弥尔》中就经常采用经验这个概念来表达他关于课程或者说教学内容的主张。博比特(F.Bobbit)指出,课程是系列的经验,是儿童和青年达到那些目的所必须有的经验。杜威则把课程视为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所获得的经验。美国课程论专家卡斯威尔(H.L.Caswell)和坎贝尔(D.S.Campbell)认为,课程是儿童在老师指导下所获得的一切经验。[2]另一著名课程论专家福谢依(A.W.Foshay)认为,课程是学习者在学校指导下的一切经验。[3]晚近的课程理论则非常强调学生在学校和社会情境中获得的经验或体验的重要性。[4](68)正如多尔(R.C.Doll)所言,公认的课程定义,已从学程的内容、科目及学程表,变为在学校领导或指导下给学习者提供的一切经验。[5]总之,用经验来定义课程,扩展了课程的内涵,因为经验既包括被称之为知识的间接经验,也包括直接经验,既包括共同经验,也包括个人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获得课程的知识定义所无法获得的功能──课程要让学习者亲身去体验,使课程包括学习者占有和获取知识的主动过程。另一种观点认为课程是活动,是受教育者各种自主性活动的总和。学习者通过与活动对象的相互作用实现自身各方面的发展。如美国《新教育百科辞典》“课程”条目明确写道:“所谓课程系指在学校教师的指导下出现的学习者学习活动的总体”[1](177)。然而,美国学者泰勒(R.W.Tyler)在比较分析了学习活动和学习经验的区别后认为,唯有学习经验,才是学生实际认识到的或意识到的课程。因而有关课程是活动说仍可划归课程即经验的范畴。
概言之,课程知识观强调向学生传授学科的知识体系,但容易忽视学生的情感陶冶、个性培养和师生的相互作用。课程经验观强调课程应关注学生学到什么而不是教师教了什么。课程活动观不仅把课程的重点从教材转向个人、从学习结果转向学习过程,而且还突出强调了课程的实践环节──学生主动参与的学习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生个体经验获得的方式问题,即经验要通过主体活动才能获得,因而有助于课程计划的顺利实施。因此,我们在强调课程即知识的同时,应注意吸收和引进国外课程即经验、课程即活动的思想,这对于完善课程理论和深化课程改革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从课程的层级结构来看,中国学者注重课程的计划水准,即按计划进行学科教学的进程。有人考察并界划了课程的三个标准:一是计划水准(意图、记述、文件等),二是实施水准(儿童实际的学习内容与学习经验),三是结果水准(不是现实的学习结果,而是只限于计划中所期待的结果)。[1](177)显然,中国学者在课程层次上强调的是计划水准。比如,《教育大辞典》对“课程”条目的解释是,泛指课业的进程。也有人认为,课程是指一定学科有目的有计划的教学进程。[6]还有人认为,课程即教学内容和进程的总和。李秉德指出,课程即教学和学生各种学习活动的总体规划及其进程。潘懋元认为,教学内容及其进程的总和就是课程。等等。
西方学者则既重视计划水准,也强调实施水准和结果水准。比如,课程论专家塔巴(H.Taba)和比彻姆(H.A.Beauchamp)就都注重计划水准,塔巴认为,“课程”是学习的计划[7];比彻姆认为,课程是书面文件,可包含许多成分,但它基本上是学生注册入学于某所学校期间所受教育的计划。[8]例如:奥利沃(P.Oliva)和约翰逊则侧重于课程的结果水准,奥利沃认为,课程是“一组行为目标”[9];约翰逊认为,课程是一系列有组织的、有意识的学习结果。[10]另外还有些人则比较关注课程的实施水准──学习经验,比如,他们认为,课程是学习者在学校环境中获得的全部经验[11];课程是“学习者在学校指导下获得的全部经验”[12]。此外,美国学者古德莱德(J.I.Goodlad)对课程作了另类的划分,他认为,存在着五种不同的课程:1.理想的课程(idealogical curriculum),即指由一些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课程专家提出应该开设的课程,其影响取决于是否被官方所采纳;2.正式的课程(formal curriculum),即指由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和教材,也就是列入学校课程表中的课程;3.领悟的课程(perceived curriculum),即指任课教师所领会的课程,不同教师对正式课程的理解、解释方式各不相同;4.运作的课程(operational curriculum),即指在课堂上实际实施的课程,这与领会的课程又有差距;5.经验的课程(experiential curriculum),即指学生实际体验到的东西,因为每一个学生对事物都有自己特定的理解,两个学生听同一门课,会有不同的体验或学习经验。[13]古德莱德的这种层次划分建立在对课程实践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不同的课程定义在各个层面上的不同适应性,因而有助于人们对课程概念所具有的实用性意义的理解。
要言之,强调计划水准的课程,往往会使教师把目光放在可预设的教学计划和可观察的教学活动上,而不是放在学生的实际体验上,从而造成课程实践中的本末倒置现象,即将教学计划和活动本身作为目的,而忽视计划和活动的真正意义──促进学生的学习与发展。结果水准的课程观,关注预期的学习结果或目标,把课程重点从手段转向目的。实施水准的课程观,强调课程是指学生体验到的意义。应该说,课程的这几个层次各有独特的作用,它们是互补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在历来比较重视课程的计划水准的中国,吸收西方国家结果水准课程观和实施水准课程观的合理成分,无疑对于改变我国教育中长期积存的“见物不见人”“本末倒置”的课程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从课程所具有的功能来看,中国学者注重课程的社会作用和功能。比如,吴康宁认为,课程是社会的法定文化或法定知识;[12]吴永军认为,课程是社会建构的给学校师生提供可以互动的法定知识,[14]课程是由社会决定的,具有社会性,也就是说,课程是实现个体社会化的重要载体。西方学者则既强调课程的社会功能,又强调课程的个体功能。如劳顿(D.Lawton)和艾普尔(M.W.Apple)就比较强调课程社会功能,劳顿认为,课程在本质上是社会化的一种选择。[15]艾普尔认为,课程是意识形态的抉择。此外,还有人认为课程是社会定义的或社会建构的进入学术知识或行为知识的一系列的途径,其目的在于传递特定形态的知识贮存,以建构控制学校的人认为有价值的社会现实,等等。[16]同时,西方也有人强调课程的个体功能。如马斯洛、罗杰斯等人都认为,课程的作用是为每一个学习者提供有助于个人自由发展的圆满经验,他们要求通过课程将学校教育全部纳入儿童的生活,要求把课程内容本身当做重要的目标,使之成为每一个儿童的自我经验,从而促使个人的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17]
简言之,强调课程的社会功能,不论是课程即社会文化
再生产说,还是课程即社会改造说,都是将课程的重点从学校学生转向了社会而容易忽视学生的个性培养。然而,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教育的社会功能的实现取决于教育所培养的人。因此,借鉴西方个人化取向的课程定义,有利于正确把握课程的科学内涵,深化对课程社会化功能和个性化功能相统一的认识。
第四,从课程的形态来看,中国学者强调更多的是学科课程、分科课程、显性课程和必修课程。学科课程是以科学文化遗产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各门学科系统的总称。学科课程是分别地从各门科学中选择部分内容,按各门科学固有的逻辑,系统地组成各种不同的学科,并彼此分立地安排它的顺序、学习时数和期限。分科课程即指一种以各门科学体系为基础,选择其中部分内容,组成各门不同的学科,再以各学科体系为核心,彼此分立地设计各门科目内容的类型。分科课程是一种单学科的课程组织模式,它强调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强调一门学科的逻辑体系的完整性。核心课程是课程体系中居于核心的位置的具有生成力的那部分课程,它与课程体系的其他部分(边缘课程)形成有机的、内在的联系。必修课程是指同一学年的所有学生必须修习的公共课程,是为保证所有学生的基本学力而开发的课程。显性课程是由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必须接受的课程,它是以直接的明显的方式呈现的,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学习活动,学生参与这类课程是有意识的,这类课程主要是依靠知识的传递进行的,学生通过这类课程的学习所获得的主要是学术性知识。
西方在关注上述课程的同时,更注重活动课程、综合课程、隐性课程和选修课程。活动课程是以学生的主体性活动经验为中心组织的课程,它着眼于学生的兴趣和动机,主张通过一系列的由学生自己组织的活动,使学生获得经验、培养兴趣、解决问题、锻炼能力。综合课程是指有意识地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学科的知识观和方法论去考察和探究一个中心主题或问题的课程组织取向。综合课程是一种多学科的课程组织模式,它强调学科之间的关联性、统一性和内在联系。选修课程是指依据不同学生的特点与发展方向、允许个人有所选择的课程,是为适应学生的个性差异而开发的课程。隐性课程,按照中国学者的理解,即学生在教学计划以外所接受的潜在教育历程。[18]西方学者一般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从学生社会化方面理解,认为学校的中心职能是使学生社会化,使学生接受社会价值,并成为学生个性品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社会化中蕴含的社会关系结构,便是隐性课程;二是从知识社会学的方面理解,认为学校知识结构内容在形成中所隐含着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讯息即隐性课程。[19]早在20世纪初美国的杜威、克伯屈就曾深刻地阐述了人类随显性课程而生的隐性教育(主要是价值、态度)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意义,晚近的课程理论又从社会、个体等多维度对隐性课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显而易见,中国学者强调课程定义的知识取向以及课程分类的分科取向,大多主张分科课程,崇尚学科取向的核心课程观。西方学者的课程划分,不仅仅指学科课程,还包括活动课程。西方学者强调课程定义的经验取向、社会取向、学科取向和混合取向四种核心课程观,认为儿童经验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完整统一的,因而特别注重课程的动态性和综合性。在核心课程和边缘课程的关系上,中国学者倾向于非主导与依附的、有机的、生成性的关系,主张使用核心课程和拓展课程,以体现拓展性课程是在核心课程的根基上发展出来的,是变通和拓展了的核心课程,与核心课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4](297)西方学者更多地强调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认为它们是一种主导与依附的关系,必修课程的价值取向是公平发展,选修课程的价值取向是个性发展。中国由于受历史文化传统思想的影响,强调课程的整齐划一,为每个学生提供相同的教育,必修课程占据主导地位,选修课程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近几年有所发展进步。西方的选修课程可以追溯到1810年德国教育家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到20世纪初,选修课程制度开始席卷欧美大中学校。在美国,不仅高中,而且在初中阶段也普遍开设选修课,一所学校可以开设几十甚至上百门选修课,成为美国教育一道极有特色的风景线。
总之,课程是为受教育者提供的一系列的学习机会,就其内涵而言,它包括学科知识中心课程或能力为本的课程,还包括诸如澄清价值观念的经验在内的经验课程等;就其外延而言,它涵盖了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选修课程与隐性课程等,但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习性不同、教育运行机制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等等,因而对课程概念的理解与阐释难免不各取所需、各有侧重,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所以对它作一换位的比较和思考,进而为我国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提供不同的观察视角,就显得十分必要和有意义。
参考文献:
[1]钟启泉.现代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2]H Caswell,D Campbel.Curriculum Development[E].New York:American Book Company.1935.
[3]A W Foshay.Curriculum[A].Ebel,R L(ed).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Research[C].New York:Macmillan,1969.
[4]张华.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5]R C Doll.Curriculum Improvement:Decision—Making and Process[Z].1964.15.
[6]吴杰.教学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5—6.
[7]H Taba.Curriculum Development:Theory and Practice[M].New York:Har Court,Brace,World,Inc,1962.214.
[8]G A Beauchamp.Curriculum Theory(2d.)[M].1968.6.
[9]P Oliva.Developing the Curriculum[M].Boston,MA:Little Brown,1982.6.
[10]M Johnson.Refinitions and Models in Curriculum Theory[J].Educational Theory,1967,17(2):127—140.
[11]Richard D.Vonscotter and Others,Foundations of Education-social Perspective[Z].1979.272.
[12]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Research[Z].1860.358.
[13]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11.
[14]吴永军.课程社会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0.
[15]D Lawton.Class,Culture and the Curriculum[E].RKP,1975.5.
[16]P W Musgrave.Knowledge,Curriculum and Change[Z].Angus,Robertson,1973.
[17]靳玉乐,黄清蓉.课程研究方法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6.
[18]陈玉琨.现代教育管理技术[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106.
[19]陈玉琨,沈玉顺,等.课程改革与课程评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4.
(责任编辑:刘启迪)
Curriculum: A View of the Cross-culture Comparison
YANG Tian-ping , FAN Shi-wu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Zhejiang 321004,China)
Abstract: When examining and comparing the concept of curriculum from the view of cross-culture,the scholars of the east tend to interpret it as teaching plans and teaching contents of subject, and focus on divided curriculum, disciplinary curriculum, dominant curriculum and compulsory curriculum, and lay great emphasis o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curriculum. The scholars in the west,however, regard curriculum as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activity and the unity of them, and pay great atten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of activity,integrated curriculum ,hidden curriculum and selective curriculum while attach more importance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s.
Key words: curriculum; cross-culture compari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