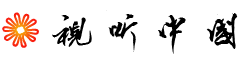从“边缘状元”看明清士林的精神转向
作为国家选拔“公务员”的一项制度,科举并不是选拔“著名文学家”,而是选拔优秀的治国理政人才。这就造成了士林人格的两重性,尤其是状元,首先应该是政治的,然后才是文化性情的。如果错位,对国家而言是“事故”,对状元个人而言就是“故事”。下面就来说点与正史不同语境的状元故事。

首先出场的是弘治三年(1490)状元钱福,《明史》里连个本传都没有,来看其他史料中的钱福简历:钱福(号鹤滩,1461—1504),华亭人(今上海)。弘治庚戌科会试第一、廷试第一,钦点状元。小时候,钱福得了一种奇怪无比的毛病,差点送命。不久,其父做了一个梦,有人对他说:“你儿子就是吴宽哪!”吴宽是成化八年(1472)状元,官一直做到了礼部尚书。据说钱父做梦时,吴宽还没有高中。后来,钱福与吴宽竟同年去世。笔记里就是喜欢记些“怪事”吸引眼球。比钱状元稍晚的陈洪谟点评说:“(钱福)为人落魄,不自珍重”,结果“以行检不立,考察作有疾黜退”。
钱福的前半段科举人生真的和苏州人吴宽很相似,但人生的下半场却大相径庭,问题大概就出在“行检不立”上。冯梦龙《古今谭概》有钱福轶事一条:
钱鹤滩(福)已归田。有客言江都张妓动人,公速治装访之。既至,已属盐贾。公即往叩,贾重其才名,立日请饮。公就酒语求见。贾出妓,衣裳缟素,皎若秋月,复令妓出白绫帕请留新句。公即题云:“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
褚人获《坚瓠集》也收录了这条笔记。听到外地有位美姝,已经退休的钱福竟立马打扮一新奔去求见,士林中可能看作是“性情”,而在道统看来就是“老不正经”了。这首诗打的是油,写的是盐,搅翻的是醋,真有“文化”啊。但卖弄的是才情,丢掉的却是状元声誉。可见当时对士林性情的评判明显因位置不同而有不同标准。
第二位出场的状元叫康海(字德涵,号对山,1475—1541),康海的名气比钱福要大得多。他不仅是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还是明代“前七子”之一,创立了自己的文学流派。《明史·康海传》只有几行字,如果把他看作著名文学家显然是远不够的,但正史把他当状元来评价,仅给几行字,说明康状元是国家的一个政治“事故”。
康海是武功人(今陕西武功),与太监刘瑾算是陕西老乡。尽管《明史》本传上说“(刘瑾)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但与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弄权太监同乡,终究要弄出是非来。《明史》本传接着写道,同为“前七子”的大名士李梦阳因直言下狱,写了张纸条让人带给康海,上书“对山救我”。康海为救朋友,无奈去找刘瑾。“瑾大喜,为倒屣迎。”这是个相当隆重的动作。第二天,李梦阳就被释放了。可见刘瑾对康海确实很看重。
士林讲究人品,而政治只有输赢。康海为朋友两肋插刀,彰显了书生性情,却因此卷入了政治斗争。随着刘瑾倒台,康状元的政治生命也画上了句号。作为状元的康海死了,但作为文化人的康海变本加厉地活了下去。《明史》本传记述道:
(从此)挟声伎酣饮,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怫郁。九思尝重赀购乐工学琵琶。海搊弹尤善。后人传相仿效,大雅之道微矣。
喝酒买醉,沉湎声色,还干起了乐工的勾当,以此消解心中郁闷。九思即王九思(字敬夫),康海的老乡,弘治九年(1496)进士。也因刘瑾案牵连被勒令退休。正史的后两句点评分量相当重,几乎把后来士风式微归结到康海身上了。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了康海一条:
康对山常与妓女同跨一蹇驴,令从人赍琵琶自随。游行道中,傲然不屑。
名士妓女共骑一头驴,驴还是瘸腿的,小厮抱个琵琶跟在后面跑,场面确实够招摇的。《古今谭概》等多种笔记收录了这段轶事,可见影响之大。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有“康修撰海”传略一篇,比《明史》详尽多了,不仅记录了康海为救李梦阳与刘瑾的对话,而且还记述了康海罢归后声伎之外的一段轶事。有一天,杨廷仪去看望康海。杨廷仪是下面马上出场的状元杨慎的叔叔、杨廷和的弟弟,兵部侍郎。老友相见,康海又是劝酒,又是琵琶表演助兴,场面十分欢快。杨廷仪见机就劝了康海几句,来看看:
杨言:“家兄在内阁,殊想念,何不以尺书通问?”德涵发怒,掷琵琶撞之。杨走,追而骂曰:“吾岂效王维,假作伶人,借琵琶讨官做耶?”
人家毫无恶意,而是出于好心的朋友之言,却引起当事人大发脾气。康海这样的做派,已不是为了消解块垒,而完全像一头受伤的敏感小鹿,不仅状元形象荡然无存,作为文化人的方寸也已大乱。钱谦益因此还惋惜了几句,说康海本来有“经世之才”,吟诗作文无非是业余爱好而已。弄成这副模样,实在是太可惜了!作者:简雄
(摘自《浮世悲欢:明清笔记小说中的士林冶游生活》)
作者微访谈
新华书房:首先请您谈谈这本书书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我看到副标题里还有“士子甲”“美姝乙”的字样,为什么要选择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历史配角”为观照对象?从他们身上反映了明清士林哪些文化特征?
简雄:这本书和我上一本《浮世的晚风》一样,关注的是明清江南士人的生活和交游情况。从余怀《板桥杂记》、钮琇《觚剩》以及钱谦益等浩瀚的明清笔记中寻找相关资料,还原那些实实在在活着的士与姬的日产过生活途径。完整的历史故事除了钱谦益柳如是、侯方域李香君等名士悦倾城的著名角色,还有“士子甲”“美姝乙”,他们存在过,被记录过,没有他们,明清之际士林“醉卧花丛”的现象就只是个例而非一个现象,士林群体与风月场交集,由于有他们,才谈得上是“高浓度”的交集,印证“家家夫婿是东林”的时评。
《浮世悲欢》和《浮世的晚风》关注的其实都不是正史中的高头讲章。本来也是历史的另一种切入点和观照方式。只是《浮世的晚风》中的人物因为戏剧等文学作品的流播而更为我们所熟知。如果真要从历史影响力来谈,勋贵名家,也往往被传统史家忽略为一个历史配角。关于明清易代之时的士林,清代就有许多反思,在思想界学术界,为黄宗羲《明儒学案》,在文艺界,为《桃花扇》。桃花扇是知识分子的侧面,晚明江南社会的背景图,进而成为解读晚明知识分子风貌的一个切入点。“士子甲”“美姝乙”是昆曲《桃花扇》中站在侯方域李香君身后的李小大、李湘真等等,共同营造江南士林高墙里的盛宴。
新华书房:经过您的研究,明清之际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士林群体却大面积“醉卧花丛”,出现这种情况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士林为何脱离正常的政治参与?这本书与您一项名为“明清江南士林文化传播力”的研究课题有关,经过您的研究,明清江南士林文化传播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简雄: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是江南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传统的四民阶层发生变化,最典型的就是士商相杂,士林的文化话语权遭到拥有经济话语权的商人的直接挑战,本书除挑选了几个士商争斗的故事外,还引用了万历年间在南京瓦官寺,苏州籍官员王世贞和徽州籍官员詹景凤的一段著名对话,所谓士商“蝇聚一膻”就出于此典。二是政治对士林的酷虐,学者称之为“一个苛刻的时代”,廷杖、弃市常常发生,《明儒学案》里有案例竟将这种黑暗自嘲为“酷”。三是心学兴起,思想企图“群体性突围”,《明史·儒林传》序言就评论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四是科举道路的壅塞。有学者考订当时的读书人人数,约有百万。但每三年一轮的科考,成功者凤毛麟角。一腔报国无门,“三袁”之一袁中道的牢骚最为典型:“不得已逃之游冶,消磊块不平之气。”
本书引用傅山的一段史料,最能说明“精英”士林与“非主流”风月场闹出这么大动静的根本原因,傅山说:“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
但士林从来都是以“修齐治平”为使命,政治上的“失意”须通过其他渠道来释放,著述立说、结社交游、书院讲坛、清议雅集成了显示文化传播力的主要形式。为了与红尘之“俗”区别,士林追求日常生活之“雅”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江南园林就可以作为一个“物象”加以深入探讨。选择“明清士林文化传播力”这样一个研究课题,还和媒体人的职业有关,因为历史就是昨天的新闻,而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新华书房:江南士林对民间的影响有哪些,这些影响是否今天也有遗留,可否举例说明?
简雄:唐代的贵族文化、宋代的雅文化还停留在上流社会和士林群体,与民间俗文化还有较分明的区分,而明代的雅文化因士林阶层和官商的融合和传播形式的改变,对民间文化也产生特别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江南地区,出版业极其发达,坊刻迎合市民需求,催生一批不得志的文人投身通俗文学的创作。才子佳人题材因这批文人的热爱和自身经历以及受欢迎程度,成为畅销题材,这些题材推动了文化产业链的形成:戏曲、评弹等市民最接受的形式有了源源不断IP。反过来,民间的文化需求与江南士林文化互相影响,表现为江南文风从雅致而向雅俗共赏的文艺转变。昆曲向其他戏剧形式提供素材被借鉴进而其主流地位被取代的过程,是士林雅文化影响民间文化,进而融合、变为民间俗文化的一个代表。士林雅文化对江南整个雅文化的推动非常巨大,生活方式的雅逸,工艺匠作的精雅(如刺绣中的书画文人绣、雕刻中顾二娘制砚受文士追捧),甚至名姬们为迎合士林群体所创的雅致的船菜,都一直流传影响至今。
新华书房:您这本书虽然是写历史,但行文颇为轻松,故事性很强。现在很多历史爱好者似乎都在追求这种亦文亦史的写作方式,您觉得这种写作的原则是什么?
简雄:作为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我结交了不少史学界的老师,首先我对“高头讲章”非常敬佩,这是历史写作的基础。本书附录一篇余怀的考订就是想表达,这是基本功。其次,涉史写作,不管文笔如何活泼,必须素材有根,言而有据。文学需要虚构和想象,但史作的文字却需要最大限度的克制,这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和爬梳来打底子。其实,中国历史上的历史书写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如《史记》以及一些正史的人物列传,《文心雕龙》里早有“法奇”“法正”的论述,明清的文坛大家如钱谦益就传承了这一中土写作方法,他的《列朝诗集小传》就很有趣。只是我们以前把它弄丢了。交汇点记者徐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