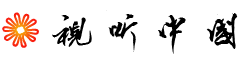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超越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集中反映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根据黑格尔的论述,市民社会概念可定义为: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属于客观精神发展的第三阶段即伦理范畴,是介于家庭生活和政治国家之间的一个特殊领域,“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前”。
黑格尔首次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剥离出来,从学理上完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由重合到分野的历史过程。在关于市民社会的问题上,黑格尔以前的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把“市民社会”与“国家”视为同一个东西。黑格尔反对传统哲学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等同公式,对社会契约论者把国家与市民社会混为一谈提出了批评,他说,“如果把国家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而把它的使命规定为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那么单个人本身的利益就成为这些人结合的最后目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成为国家成员是任意的事”。
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叫作“外部的国家,即需要和理智的国家”,以区别于他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或政治国家。这里所谓的“需要”即指人们的物质生活、物质利益的需要,它是市民社会中众多个体相互联系的纽带。在市民社会里,独立自足的个人进行生产、交易、消费,以满足各自的需要。黑格尔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不是随遇而安,而是通过劳动手段,把自然界提供的原料改造成能够满足他们多样化需要的形式。不难看出,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属于物质生活的领域,其中,“需要的体系”即社会经济关系领域,是以法律制度和公共权力为后盾的“外在的”政治秩序,因而它被黑格尔视为“外部的国家”。
当然,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亦有其缺点。他在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进行二元区分的同时,仍将司法制度和警察组织等属于政治国家的机构纳入市民社会的范围,明显地暴露出其在分离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过程中的不彻底性。黑格尔将政治国家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把前者视为决定后者的东西,这种“倒因为果,倒果为因,把决定性的因素变为被决定的因素,把被决定的因素变为决定性的因素”的观点,使他无法超出历史唯心论。此外,黑格尔高扬政治国家、贬抑市民社会,在他那里,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体现了“善”与“恶”的两极,前者是善的体现,后者则被贬为“个人私利的战场”。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固然有得益于黑格尔的地方,但二者的差异是主要的。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不再是黑格尔意义上被贬抑、处于被政治国家所决定的从属地位的概念。马克思不仅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全部历史的发源地和舞台”,而且把它改造为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并从“物质交往”“社会组织”“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的意义上加以阐释。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抽象性和神秘性,并由此步入唯物史观的门槛。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始终站在现实历史和社会的基础上,从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出发,从“物质生活关系”出发来解释“市民社会”。
在标志唯物史观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完全变成了社会差别,即没有政治意义的私人生活的差别。这样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的分离的过程”,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独立存在,“市民社会的成员在自己的政治意义方面脱离了自己的等级,脱离了自己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实际地位”。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既不是人类社会中的永恒现象,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它有其特定的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市民社会”是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社会经济关系和物质交换关系的体现,是商品经济和私人利益的必然产物。它存在于国家和家庭之间,存在于一切有商品经济的时代,对私人利益和国家普遍利益的矛盾起着调和作用。
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马克思主张“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沿着这一思路,马克思把社会存在分为市民社会和国家两个方面。市民社会构成社会存在的物质生活领域,以物质生产活动为主要内容;国家则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政治生活领域,以政治活动为内容。他指出,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市民社会的成员组成了国家;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促成了国家;市民社会的目的和任务呼唤着国家。市民社会是国家决定性的因素,是国家产生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人类生活和社会结构的两个不同层面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并由此得出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标志着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在揭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正确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两者的关系提升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高度。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治制度及思想意识观念是从属性的、第二性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则是决定性的、第一性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市民社会,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国家。马克思说:“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作为人们在生产和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物质关系,以及直接从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冲突决定历史的发展,是通过市民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如果人们的分工发生变化,人们的劳动资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发生变化,那么,人们在生产、交往中的物质关系、人们的经济组织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最终会引起国家及其他上层建筑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总之,“市民社会”从一个被黑格尔所贬抑、处于从属于国家地位的概念,到被改造成为构筑唯物史观理论大厦的重要范畴,在这个不断提升的过程中,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超越,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根本性转变。